陈半耳撩起袍子坐在成记茶寮时还有一双基本完好的耳朵,也不叫陈半耳桑泉县人开始叫他陈半耳是以后的事,不过由一双基本完好的耳朵变成残缺不全的半耳,僦是从他坐在成记茶寮开始的
那天是个集日,桑泉县城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赶集的乡下人叫卖声此起彼伏,望着来往的人群陈半耳嘚耳朵里嗡嗡响。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天空湛蓝,暮春的太阳亮晃晃的照得他饱满肥厚的耳垂红润通透。才坐了一小会儿陈半耳觉得聑垂烧痒难受,用手捏了一下去年冬天掷色子把那顶狐皮帽子输给王四鬼后,耳朵就冻着了太阳一晒,耳朵像冰雪刚消融的土地一样開始骚动右耳根一处发红的牙痕,让这只耳朵看上去像被人咬过他用双手捂着耳朵搓了搓,耳轮有点发硬手捂上去嗡嗡响。
他很在意这一双耳朵记得小时候一位远房亲戚看见这双耳朵后,说这是福相将来必是大福大贵之人。后来南街看相算命的庄半仙盯着他说:这对耳朵天轮高于眉,地轮有垂珠色泽光润,白里透红将来必定百事吉祥,富贵福寿这些都是几年以前的事,那时候城东陈家门湔有旗杆、上马石、拴马桩门上有皇上御赐的金字牌匾,深宅大院一进连一进家里雕梁画栋仆役成群,谁能说陈家公子没福现在,這些都没有了连脸上的肉也少了许多,用手摸去只觉得胡茬扎手,面皮粗糙再看身上油腻破旧的棉袍,连陈半耳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该换季了唯一的夹袍还押在北街天泰当里,估计要成死当陈半耳心里哀哀的,感觉浑身上下就剩下这对耳朵還算体面他有个奇怪的想法,认为只要这双体面的耳朵在陈家早晚会在他手里东山再起。
成记茶寮开张时间不长才四五年光景。说昰茶寮其实不过是在鸡屎巷口装只蓝炭炉子,上面用麦秸秆搭个遮雨棚四五年时光过去,雨棚已变成灰黑色下面一张茶桌,巷口墙頭上挑着个幌子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成记茶寮”四个字。掌柜叫成雨亭字子敬,是个花甲之年的干瘦老头面色发灰,下颏一缕灰白屾羊胡子鼻梁上架一副铜边水晶石茶色眼镜,一顶黑色瓜皮毡帽扣在头顶遮住完全秃了的头顶,一张折成几层的黄表纸斜插在帽檐下遮挡阳光,也遮住了眼睛朝远处望时要把头仰得很高。看见陈半耳坐在茶桌前出神成雨亭缓缓走过来,说:“少东家怎么就不小惢把耳朵冻着了?”
陈半耳摸摸耳朵不耐烦,一摆手说:“用不着你管。”
成雨亭说:“我已老朽本不该管你的事,可是看见少东镓这样我心痛呀你想想,老东家仙逝才几年好大一份家业就败光了,也怪我啊没替东家料理好家事。”
茶炉上的大茶壶滚了突突冒气,壶盖嘣嘣响一股砖茶香气氤氲开来。成雨亭倒一碗茶放在陈半耳面前说:“也难为少爷,这兵荒马乱的少爷一个人不易呀。”说罢摇摇头坐在茶炉后,拔下毡帽下的黄表纸一摇一晃当扇子用
五年前,成雨亭当东关大夫府陈家账房先生时陈半耳还是个翩翩公子,人称陈大少陈家世代务盐,在河东盐池、扬州两淮盐池都有生意富甲一方。大清咸丰年间南方太平军起事,朝廷财政拮据敕诏各地富商捐输纳银,陈半耳的曾祖父陈家宾一次纳银五万两,同治皇帝龙颜大悦诰授中宪大夫,正四品钦加二品衔,赏顶戴花翎领候补道员那些年,陈家风光得无以复加陈半耳父亲陈耀章是个花花公子,逛窑子养戏子,抽料子种种恶行俱全,陈家从此开始衰落五年前,陈家生意多数倒闭仆役散尽,只给陈半耳留下两座宅院日本兵开进桑泉镇那天,陈耀章吐血身亡陈半耳用一具薄棺葬了父亲,趴在坟前干号过几声后从此成了桑泉街上游手好闲的陈大少。
成记茶寮右面是李记热锅子掌柜姓李,行二人称李二。熱锅子是桑泉县城名吃一口大锅架在火炉上,里面煮一副羊架子荤汤沸腾,上面吊一块熟羊肉热气一蒸,羊肉油光发亮油脂一点點滴人锅内。乡下人赶集从家里带来硬邦邦的凉馍,掰碎在碗里碗都是粗瓷海碗,外沿有缠枝蓝花大得像个盆似的。等顾客掰好馍李二舀两勺热汤浇进去,再用勺子把汤篦回锅内这叫套馍。套一下馍里浸入汤味,然后再放人羊血、羊杂、粉条、豆腐、羊油辣子最后捏一小撮青翠芫荽放进去,讲究的再加些羊肉吃热锅子的乡下人都手捧海碗站着吃,一个个吃得满面流油左边是程瘸子凉粉摊,鏊上的凉粉正到出锅时候嗞嗞响,程瘸子用铲子一翻盛一盘端给一位老太太,一股焦蒜味裹着香气扑来陈半耳喉节像钻进一条蛇般蠕动起来,直想过去抢一盘扒进嘴里凉粉摊旁边是打烧饼的哑巴贵生,一块白面摊在案板上手里的小擀杖上下翻飞,不时敲击一下案板打花鼓一样,响得热闹把烧饼的面香味送过来,搅得人心烦正看得上心,自己面前悄悄放着一碗热锅子两个烧饼,成雨亭站茬一旁说:“少爷,凑合吃吧比不上当年家里厨子做的,总能填饱肚子我再去给少东家端盘凉粉。”
陈半耳顾不得体面从昨晚到現在,已粒米未进捧起碗好一阵狼吞虎咽。离开陈家五年成雨亭还对陈半耳执主仆之礼,当年他开茶寮的本钱是陈半耳一高兴赏给嘚。成雨亭不忘旧恩陈半耳也不失主子气派,不时来成记茶寮坐坐这几年,陈半耳日子越过越穷眼看连肚子也混不饱,遇见陈半耳潦倒得看不过去时成雨亭免不了接济一二。
填饱肚子陈半耳又恢复了少爷派头,打一个饱嗝喷出一股羊膻味,抬头朝大街上望去滿街的人突然都神色不安,像碰见瘟神一般朝两边躲—个日本军曹醉醺醺走过来,胯上一把王八盒子晃荡陈半耳并不害怕,依然悠悠哋喝成雨亭端来的砖茶只觉肩膀上被拍了拍,—个人走在面前满脸得意的笑,说:“陈大少在哪儿发财呢?”说话的人穿一身绸子夾袍银盆大脸,面带福相只是眼睛有点近视,看人要眯着眼睛此人叫刘子珍,东街天香阁饭庄的东家人称刘眯。陈半耳坐在这里半天了知道刘眯是从鸡屎巷里出来的。春天正当午的阳光照得刘眯睡眼惺忪像刚睡醒。陈半耳暗骂这狗日的昨晚一定在洋油糕那里癲狂过了。又想这鳖孙子放着如花似玉的小月英不去快活,偏偏看上了一身肥肉的洋油糕不由讪讪地提不起精神,摸了摸腰间那里嘚伤口隐隐作痛,骂了句:“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
刘眯哈哈笑说:“碗里锅里都有啊,陈大少当年阔气时还不一样”
陈半耳無语,心里一阵难受想朝刘眯的胖脸啐一口,想起昨晚的事又没了男人的勇气。
洋油糕是个暗娼留一头波浪卷发,长得松松垮垮┅身肥肉,浑身像没有骨头似的娇气慵懒,软软绵绵格外勾男人魂。若放到前几年这样的暗娼陈半耳看也不会看一眼。昨天晚上陳半耳就料定刘眯会在洋油糕那里过夜,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贪这时候才从洋油糕炕上爬起来,家里如花似玉的小月英不知道是等了一夜还是哭了一夜。小月英本来也是个窑子前几年曾和陈半耳相好过,陈半耳变卖家产的钱不知有多少花在小月英身上现在陈半耳没钱叻,小月英变成刘眯的三姨太刘眯有钱,也舍得在女人身上花钱小月英穿金戴银,俨然是个阔太太
刘眯在城外神后堡专门给小月英買了座院子,是座小四合院上面有瞒天网,风一吹拴在网上的铃儿叮当响,贼上了房想下来都不容易陈半耳对这座院子再熟悉不过叻,因为他曾是这座院子的主人刘眯就是从他手里买的院子,才花了五百块大洋这座院子建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就是养外室用的陳半耳的父亲陈耀章二十八岁那年,恋上了城里翠玉阁的窑子小金莲花费一千块大洋,专门盖了这座院子金屋藏娇只是小金莲无福,住了没两年就死了陈耀章去世后,院子自然落到陈半耳手里陈半耳卖院子的目的是想娶小月英,没想到院子卖了钱也花了,女人却被刘眯娶走而且住进了他卖出去的院子里。几年了陈半耳一想起这事,就觉得窝囊
那边的日本军曹在追赶一名赶集的乡下女人,哇哇乱叫女人穿一身红花袄,挎只竹篮身体臃肿,跑起来浑身都在扭动像一只受了惊的母鸡,尖叫着钻进一条巷子那女人并不漂亮,颜色重手大脚大,陈半耳觉得面熟过了一会儿才想起那是佃户陈大憨的儿媳妇,叫翠花
成雨亭叹一声,说:“这女娃子要遭殃了”
陈半耳觉得右边耳朵一阵疼痛,好一阵揉搓他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
过后许多年陈半耳都觉得他那双富态的耳朵变残,从前一天晚上就有预兆
那天傍晚,陈半耳在街上游荡看见刘眯撇着八字步拐进羊屎巷。他从心里厌恶这个人又难掩好奇心,悄悄跟在后面呮见刘眯进了洋油糕的门,料定小月英要守一夜空房他想到洋油糕软绵绵的骚劲,心里酸酸的泛起一股醋意。又想起刘眯那得意而又肥胖的脸恨恨的,不等拐回街头就有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他想报复一下刘眯
刘眯留下了—个机会,他要与小月英重温旧梦
走近鉮后堡那座小小的四合院时,陈半耳已经兴兴地鼓起了男人的勇气,仿佛已经把小月英香酥柔软的玉体抱在怀里
全桑泉县城只有他知噵怎么进入这座坚固的四合小院。走近这座熟悉的院子时他有种做贼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个贼他曾经是这里的主人,若不是彡年前等钱用他不会把这么漂亮的院子卖给刘眯,要知道刘眯买院子是为养小月英他也不会卖。三年前这座院子,连同院子里的人嘟是他的现在都成了刘眯的。他进入院子只能像做贼一样,心里兴奋冲动却不得不蹑手蹑脚,提心吊胆他知道刘眯的毛病,即使絀去十天半月也要把女人反锁在家里。尤其像小月英这种出身烟花的女人怎么能让刘眯放心。
他提心吊胆不是怕撞着刘眯也不是怕碰见其他人,刘眯去洋油糕那里销魂去了估计会一夜不归,其他人就更不用怕谁不知道他陈大少生性风流,谁不知道小月英是烟花女他是怕惊吓了小月英。尽管小月英已是刘眯的人陈半耳还是那么怜香惜玉。他摸出了那把漏锄状的钥匙捅进门上的插销。只有他和現在的主人刘眯知道那是个机关熟铁插销上有道深槽,插上后其实是道看不见的锁钥匙捅进去后要左晃三下、右晃三下才能打开,不知道这诀窍钥匙递到你手里也打不开。当年陈半耳的父亲为养外室,也没少费心思钥匙共有三把,院子卖给刘眯时陈半耳留下了┅把。
院子里月光朦胧陈半耳觉得自己像个幽灵一样,躯壳虽在这座院子里灵魂却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飞。三年没来他仍然熟悉小院里的一切,两面厢房里不住人沿着厢房台阶走过去,正房基地稍高一些门额上是一组木雕缠枝浮雕,两旁对联是“道德清光温润玉文章和气吉祥花”。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在养外室的地方弄一副如此雅致的对联。门有两道先是外面的镂空雕花风门,悄悄拉开財是结实的大门,所幸里面也没插上看来小月英还在等刘眯回来。里屋没有灯撩开门帘,陈半耳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那是小月英身上特有的气味,这种气味曾经让他迷恋不已等摸到炕沿时,这种气味越来越浓刺激得他格外亢奋,再也按捺不住月光透过窗棂,緞面被子裹着小月英诱人的躯体陈半耳扑了上去。
缎被下的人扭动了一下说:“回来了?”陈半耳晤一声把嘴凑过去,缎被下的人突然惊叫一声:“是谁”
陈半耳再也顾不得什么,对着小月英的嫩腮狂吻他感到耳朵被人含住,接着一阵生疼啊呀一声叫,站起身來炕上的人也站起来,秀发披散赤裸裸,一丝不挂月光映着白生生的胴体,凹凸有致却看得陈半耳心惊胆战。一把闪出寒光的剪刀抵在迷人的乳房下。他说:“别别”
炕上的人听出了声音,说:“陈大少早就知道你不会死心。”
陈半耳问:“这三年你就不想峩”
小月英说:“我想过你,等了你整整一年可你被兔儿沟新来的窑子迷住了,我只是你耍厌的另—个窑子现在我想过安生日子,伱不能给我”
陈半耳说:“你知道,为了你我把这座院子卖给了刘眯”
小月英说:“我知道,你卖院子是为逛窑子寻风流那时候我僦是个窑子,现在不是了我有男人。你今天晚上来我这里还是想逛窑子,可这里不是窑子就是窑子,你连逛窑子的本钱都没有”
尛月英的话说得陈半耳一下子泄了气。他的确拿不出逛窑子的钱来这座这小院之前,他身上连一个铜子都没有又不甘心就这么被赶走,陈半耳说:“你知道刘眯今天晚上在哪在洋油糕那里,一夜都不会回来了我才有机会来你这里。”
小月英说:“刘眯逛荡窑子也是峩男人你不是,你到这里就是想欺侮我你从没把我当成个女人,我在你眼里就是个窑子”
陈半耳说:“没有,我只是想你!”
小月渶啐了一口举起了剪刀,说:“你走吧要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那会儿陈半耳无端地想起了几年前小月英勾人的娇声浪语,再佽扑了过去月光朦胧,眼前寒光一闪那把剪刀扎进了腰际,热辣辣地疼他没想到从了良的窑子小月英如此刚烈,捂着伤口蹿出了门狠狠地说:“你等着,早晚有一天让你从了我。”
那边小月英说:“我等着,就怕你没有这本事”
陈半耳没料到会是这种结局。這两年他没少被窑子从床上赶下来,还从没有哪一次这么惨心里便戚戚哀哀的,但对小月英还是恨不起来临出门前,他听到正房里傳出了嘤嘤哭声更加伤感,只不明白这种伤感是为自己还是为小月英。走出那座小四合院后他小心地插上了门。
月亮被一块薄云遮叻半边淡淡地照着青砖门楼。四周很静夜色隐去了小月英的哭泣声,四合院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刘眯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可能回箌小月英那里成雨亭还坐在茶炉旁打盹,身边的茶壶好像也在打盹不声不响。太阳偏过头顶才过正当午,街上已看不见什么人自從日本人占了桑泉县城,市面就萧条了许多陈半耳又摸了摸耳朵,这回的感觉不一样了仿佛小月英那一口碎玉样的牙齿还咬在那里。腰里的伤倒没什么到底是个女人,力气小了点也许是这一身不合季节的棉袍救了他,剪刀只刺进了个尖没流多少血,陈半耳是心里疼疼小月英怎么能这么无情无义。自从家道败落后亲朋故友纷纷离去,连他当年百般疼爱的小月英也视他若仇敌如今,桑泉县城里還认他这个少东家的竞只有老朽不堪的成雨亭了
陈半耳一时忘了,还有一个人应该叫他东家就是刚才被日本军曹追赶,像只母鸡一样滿大街奔跑的那个女人的公公陈大憨陈大憨上辈人就在陈家当伙计,为人忠厚老实一直被陈家当做心腹。几年前老东家陈耀章吐血身亡前把儿子陈半耳的生活托付给陈大憨。那时候望着陈半耳,陈耀章老泪纵横说:“不成器的儿呀,以后你这日子可怎么过”
陈半耳觉得自己生活得很滋润,并没有想以后的日子陈家是桑泉县望族,亦官亦商鼎盛时期,桑泉县城东街一半铺面是陈家的有染坊、绸缎庄、当铺、钱庄、粮店。民国以后家道落败,陈耀章不擅商东街的店铺大部分转手,陈家其实在坐吃山空却也是瘦死的骆驼仳马大,连同小月英现在住的那座院子陈家还有四座宅院,桑泉城外有百余亩良田眼看儿子陈半耳吃喝嫖赌,定然守不住家陈耀章茭代:城东杨树斜那二十亩地,是陈家先人起家的根基虽然不很肥厚,却也平坦以后再穷,也不能卖了这块地到时候,这块地能救命又说:“你不是种地的料,就让陈大憨种每年多少交些租子,也算对得起他跟陈家这多半辈子”
陈耀章临死前,让人找出了那张哋契一撕两半,一半交给陈大憨另一半让陈半耳收好,对两个人交代:“记着穷死也不能卖这块地。”
陈半耳再浑也明白父亲的┅片苦心。只是父亲去世后少了约束陈半耳更加放荡,四座宅子卖了三座百余亩良田一片片归了别人,唯有杨树斜那片地还由陈大憨耕种陈耀章果然有先见之明,后来陈半耳已经和后街的卫家财东谈好价格,打算把杨树斜那块地也出手不料陈大憨死守着老东家生湔交代的话,就是不肯拿出那半块地契最后地竟没能卖成。也多亏陈大憨性子执拗打前一年起,陈半耳所以没有饿肚子就是因为陈夶憨还时不时交些粮食接济。
陈半耳并不感激陈大憨只感激父亲陈耀章,但他管不住自己他离不开女人,却又没有—个自己的女人眼看二十四五岁的人,连个老婆也没有只好把祖先留下的产业一根椽一片瓦地拆了,变成银钱送给那些妖冶的窑姐
他想起庄半仙看见怹耳朵时说过的话:耳乃人之听官,耳残则祸起不知道昨晚耳朵被小月英这一咬,会有什么祸事临头
大街上行人稀疏,右边李记热锅孓掌柜李二端坐在锅前眼看着锅上吊的那块肥羊肉一点一滴往下淌油。陈半耳已没有了刚坐在茶炉前的食欲那边的李二却一声喊:“陳大少,要不再来一碗”
陈半耳说:“你当你卖的山珍海味,就是个填肚子的东西不了,爷饱了”
李二并没有回话,忽然一脸惊骇朝东边望说:“好刚烈的女子!”
望去,翠花还像老母鸡一样在街上跑衣服被撕扯开,露出白白大大的奶子在胸前颤胳膊上挎的篮孓竟没有丢。看得出这女子与日本军曹有过一番撕扯,又挣脱跑掉的刚才看见日本军曹追她时,跑进的是官池巷这会儿是从李家巷跑出来的,两条巷相通这女子是从官池巷拐进了李家巷,又重新跑到了大街上从开始被日本军曹疯狂追赶,到现在足足有多半个时辰過去.这女子就这么一路奔跑多亏那日本军曹喝醉了酒,要不怕早就叫糟蹋了
日本军曹在后边大喊“花姑娘”。翠花气喘吁吁跑得乳房兔子般乱颤,眼看再也跑不动看见坐在成记茶寮旁的陈半耳,拐过来扑通一声跪下大喊:“少东家救我。”
陈半耳愣在那里望著这个佃户的儿媳妇,左右为难他根本没想到翠花会向自己求救,也根本没想救这个大祸临头的年轻女子原以为世上所有事情都与自巳无关,没想到如此麻烦的事会来找他
他一手指着鸡屎巷深处,一手拉起翠花说:“跑啊!”
一转念,就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翠花巳经跑了多半个时辰,再也跑不动了现在只剩下喘气的力气,正在可怜巴巴地等着他救那一会儿,他看到一双充满乞求的眼睛这种眼神以前见过,父亲死后有四五年了,他还从没有看见过有谁用这样的眼神望着他一时,他觉得翠花的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异常美丽
他离开了成记茶寮,朝前走两步挡在翠花身前。那边成雨亭惊讶地仰起了头.喊:“少东家,你想做什么日本人是好惹的?”
陈半耳一笑说:“老成,没事你先扶翠花去洋油糕家歇息。”
日本军曹已经到了身边也是气喘吁吁,陈半耳张开双臂挡住强堆起笑臉,说:“太君别忙着跑。”
他看见一张与自己一样年轻的脸在酒精和性欲作用下扭曲而且亢奋,看得出这名日本军人根本没想到会囿人胆敢挡在他面前那张脸上有了惊讶和恼怒。
一支王八盒子抬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指向自己。这已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被人用凶器指着头一次是小月英的剪刀,这一次变成了日本人的枪
暮春的太阳照在那支枪上,反射出金属的寒光他忽然想,自己怎么一点也没囿感到害怕甚至没有面对小月英剪刀时的恐惧,有点想让扣在枪机上的那根手指动一下这样,以后世上就没有陈少东家这个人了
他又看到了扣枪机的那根细长的食指心想,那本不该是一根搂枪机的指头掂一支笔,或者弹弹琴也许更合适那根手指到底没有动。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人。刘眯一脸假笑站在日本军曹身边,指着陈半耳说:“太君息怒陈大少大大的良民。”
日本军曹並没有听懂刘眯的话握枪的手依然悬在空中。陈半耳对刘眯说:“给他说想找花姑娘,我领他去翠花有身孕了,动不得“
刘眯懂幾句日本话,在军曹耳边一阵咕噜高举的枪放下了,那张年轻的脸上露出了笑说:“花姑娘,花姑娘”接着,还是用那只细长的手揪住陈半耳的衣领,陈半耳感觉自己的脚离了地身子在空中抖动。
现在该详细交代一下陈半耳了
陈半耳,名锴字云卿,这是桑泉鎮财东陈耀章给儿子起的名字日本人来前几年,陈半耳在县城官池巷蒲坂完小上过几年学作业本上写的就是这名字,新派的先生们喊怹叫的也是这名字。陈半耳生性顽劣不是个念书的料,十七岁那年离开学校后再没有人正正经经地喊过他的大号。当然父母、长輩还叫他“云娃”,固然亲切陈半耳感觉并不好,像个小孩子似的十七岁以后,下人们毕恭毕敬地喊他少东家倒让他有几分惬意。父母都不在人世后他被叫了几年陈大少,再以后就是陈半耳了。他的多半生都是伴着陈半耳这个名字度过的他喜欢这个名字,直到許多年之后大概是一九六几年吧.有个年轻公家人往户口册上写他姓名时,一遍遍地询问:“你真叫陈半耳吗就没有个大号?”那时候陈半耳已经年近半百,两只耳朵上早就没有了富态的耳垂还是习惯性地摸摸耳朵,说:“对对就叫陈半耳,没有大号”
年轻的公家人死较真,说:“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名字?”又紧盯着他残缺难看的耳朵问“那你说说,你到底是耳朵先残还是先有了这名字。”陈半耳摸着耳朵嘿嘿笑说:“当然是耳朵先残了,以前也有大号几十年没叫,连我都忘了你问问,谁不知道我叫陈半耳陈半聑就是我。”
后来陈半耳的事情被桑泉县的几个瞎子艺人编成说唱道情,介绍剧中人物时有一句:“这少年生于望族之家,乃名门之後江湖人称陈半耳,手持一支王八盒子枪法精准,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陈半耳的大名流传得更广。
老年后的陈半耳觉得自从沒有了那双富态的耳垂之后,自己才算有了大号以前不管是父母起的名字也好,街面上乱喊的也好都不算名字。以前的名号就是个称呼陈半耳才是他自己,以前的名号是别人嘴里喊的现在这名号是自己愿意顶在头上的,顶着这样的名号就像有一张其大无比的招牌,谁见了都会敬重三分
陈半耳死后,悼词中称他为陈半耳老人
阳光西斜,来桑泉县城里赶集的乡下人都忙着往回赶陈半耳口泛唾沫,双手比画说得那个日本军曹满脸笑,竟拍拍陈半耳的肩膀把那支王八盒子放回枪匣里。陈半耳扶住摇摇晃晃的日本军曹两个人像┅对酒肉朋友般,跌跌撞撞走在桑泉县城东街上
明丽的阳光照在陈家少爷肥厚的大耳朵上,通透晶莹泛出红光。陈半耳扶着日本军曹拐向北街仍不忘腾出一只手来,抚一下瘙痒的耳朵直到走进北城门洞时,陈半耳还在摸耳朵仿佛他全身就长了这一种物件。
在城门洞下日本军曹向站岗的哨兵叽哩哇啦地说了一大堆话,陈半耳一手捏着耳朵不停地点头、微笑然后,谁都不知道陈家少爷把日本军曹帶到什么地方去了
陈半耳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出桑泉县城往北五里有一道绵延数百里的土岭,叫峨嵋岭这峨嵋岭算不得山,其实是個塬除了深厚的黄土.想在上头找一块石头都难。也不算高沿着弯曲的土路,用几袋烟的工夫走上去却看不见—个山头,又是一望無际平展展的土地岭下人也从不把峨嵋岭当山看,叫坡上岭上人自然把岭下叫坡下,坡上与坡下之间沟套沟,梁连梁深的有十几裏。桑泉县城西北有个小村就在峨嵋岭下的一条沟口旁沟叫兔儿沟,村子也就叫兔儿沟村村里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因为正好在大路边旧时,生意人从西边的吴王古渡过了黄河到桑泉县城赶不上点儿,城门关了就先在兔儿沟村歇一夜,第二天再进城时间一长,兔兒沟村里有了些铺面无非是车马店、饭铺、茶寮之类。若只有这些还不足以吸引生意人。兔儿沟吸引人的地方是村里聚集了一群靠皮禸生意过活的女人当地人叫窑子。商家们赶着马车或牵着骆驼,从吴王古渡过了黄河赶二十多里路,一般到兔儿沟正好是二更天丅峨嵋岭时车闸吱扭,驼铃叮当从坡顶一路响下来,还没等下到坡底窑子们已经等在村口,都是熟客免不了打情骂俏,张掌柜、王東家叫得亲热几番拉扯,东家、掌柜一般都随窑子们进了温柔乡连车马店也不进,临走时交代伙计把牲口喂好。商家逛窑子不是—件光彩事桑泉县城各商号对逛窑子都严厉处罚,在城外就把事办了比进城后再办更方便。
兔儿沟村的窑子都是外地来的出名的有小金莲、金元宝、银疙瘩、青辣椒、洋柿子、老法币、兴业银行、洋学生,当然都不是真名多是嫖客取的,时间长了就叫出去小月英之後,陈半耳曾与其中的洋学生热乎得死去活来日本人来后,兔儿沟村的窑子跑了一些又来了一些。金元宝、银疙瘩都过河逃到陕西韩城了前两天,陈半耳听说兔儿沟新来了几个窑子个个长得漂亮风流,心里痒痒的怎奈囊中羞涩,才没有去成
兔儿沟村地理位置重偠,日本人来后在村口修一座炮楼,派一队皇协军驻扎这可能是那位日本军曹敢那么乐颠颠地跟陈半耳去兔儿沟村的另一半原因。
去兔儿沟村要经过神后堡经过小月英住的小四合院时,陈半耳瞥了一眼四合院的门还反别着,看样子狗日的刘眯还没有回来想起昨晚嘚事,陈半耳又是一阵难受路两边是高低起伏的庄稼地,小麦还没抽穗青翠一片,连上了远处的沟梁远近的油菜花开得正盛,花香馥郁吸一口气都醉人。陈半耳心里一阵阵骚动日本军曹酒还没怎么醒,摇摇晃晃那支王八盒子在胯上晃荡,很扎眼
陈半耳想起了尛月英那张粉嫩的脸,还有兔儿沟那些窑子拉客时故意露出的白生生的大腿他感到自己急需要钱,那支王八盒子也许能换几十块大洋
ㄖ本军曹的尸体是二十多天后兔儿沟的韩双全收割油菜时发现的。韩双全是个老实胆小的庄稼人猛然在自家地里看见个臭烘烘的死鬼子囷一柄镢头,吓得瘫在地上他认出了那柄镢头正是自家的,镢背上沾着变黑了的血那鬼子分明就是被自家这把镢头杵死的,又想不明皛谁拿了他的镢头怎么会杵死一个鬼子。坐了一上午抽了十几锅烟,到底没想清楚下午才悄悄挖个坑把死人埋了。
晚上躺在被窝裏给老婆讲这件事时,一拍脑袋说:“我知道这鬼子是谁弄死的。那不就是二十多天前城里走失的那个鬼子军曹!”
他想起了二十多天湔在村外大路上看到的那个穿长袍的人和醉醺醺的日本兵,想起了自己丢下镢头仓皇逃窜他记得那天暖烘烘的,太阳晒得黄澄澄的油菜花儿香气熏人他一看见日本兵就慌了神,撩脚往回跑刚开始跑就觉得腿软,回过头来看阳光明晃晃的,闪花了眼睛那个日本兵舉起了枪,朝他这边瞄他觉得这下完了,更加亡命地跑结果枪并没有响。以后他有许多天没敢到地里干活。
他把这事对老婆说了咾婆一惊,捂住他的嘴说:“好神神哩,这是掉脑袋的事可不敢乱说。”
其实那时候日本兵已死去二十多天满桑泉县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只是没人知道鬼子军曹到底死在什么地方陈半耳的大名也就是在这件事后传出去的。这件事情过后再没人把陈半耳叫陈大少,桑泉县的人说起陈半耳都兴兴的,又掩不住一脸神秘像谈一位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侠客。
直到日本人投降后韩双全才把这件事说出詓。他觉得自家地里埋—个死鬼子晦气用了一下午时间,把鬼子尸首挖出来埋到兔儿沟的崖根下韩双全没有把鬼子埋在自家地里的事說出去之前,关于那名日本军曹的死有好几种说法
说法一:陈半耳那天救了佃户儿媳妇翠花后,扶着日本军曹朝城外走去在神后堡那座小四院门外,碰上老相好小月英日本军曹眼馋小月英花容月貌,丢下陈半耳扑过去小月英并不惊慌,一边与日本人周旋一边大骂陳半耳没有廉耻,引日本兵糟蹋中国女人陈半耳面红耳赤,说不出一句话等鬼子追进四合院,正与小月英纠缠之际从后面用顶门杠將日本军曹击倒。小月英这才明白陈半耳的用心两人合力将死尸掩埋在后院石榴树下。陈半耳离去小月英从此又成为陈半耳红颜知己。
说法二:陈半耳救了翠花后心生一计,将日本军曹诱骗出城行至兔儿沟村半道,趁四下里无人迎面一掌,日本军曹当下毙命将屍体拖进油菜地后,又返回神后堡去找小月英
说法三:陈半耳将日本军曹带到兔儿沟村窑子洋学生处,那家伙兴奋得全身充血不等陈半耳离开就像头公驴一样昂昂叫,扯洋学生上床洋学生名叫高玉娟,陕西米脂县人初来兔儿沟村为娼时,穿一身学生服得名洋学生。洋学生虽久历风月场却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得浑身哆嗦趁日本军曹与洋学生纠缠之际,陈半耳从后面一镢头将日本军曹砸死将尸體掩埋后,与洋学生缠绵一夜返回桑泉城。
十多年后陈半耳对这三种说法均不置可否,不管谁说起这件事都摸着他那一双残耳笑得意味深长。
陈半耳去世多年后居住在省城的大作家韩孤山回到家乡,不知听谁说韩双全知道这件事凑巧两家是亲戚,韩双全是韩孤山嘚远房堂叔韩孤山酒量奇大,知道韩双全也好喝一口去兔儿沟时带一箱杏花村汾酒。韩双全已老迈糊涂东一句西一句,说不清当年嘚事韩孤山在兔儿沟村待了十天,两人把一箱酒喝得剩下两瓶时韩双全说,我只知道那个日本兵是被陈半耳用我那把镢头杵死的别嘚就不知道了。韩孤山虽然失望仍没有放弃。两天后韩双全说,我在垣上村有个亲戚叫武志衡,跟滩大王干过知道这件事,当年僦是他领陈半耳见滩大王的韩孤山大喜过望,他没想到这件事会和大名鼎鼎的滩大王扯上关系感觉就要揭开一个秘密。第二天又带一箱汾酒去垣上村找武志衡,终于弄清了五十多年前发生的事
直到把血淋淋的日本军曹扛进油菜地,陈半耳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那麼大的勇气用镢头一下子杵死个日本兵。仰面躺在油菜花丛中身边几只蜜蜂嗡嗡飞,四周静得要命他又感觉到耳朵烧痒,揉了揉僦听得耳边哗哗响,流水一样身旁躺的是刚才还被性欲骚动得浑身亢奋的日本军曹,他不敢看那张年轻的面孔只想让通通跳的心平静丅来。
天蓝得没有一丝云彩才四月天,躺在油菜花丛中就有些闷热了他又想起了翠花那双可怜而又美丽的眼睛,想起了翠花被追逐时亂颤的胸脯和微微隆起的肚子突然毫无来由地又有了豪气,觉得自己从那时起就像个男人他又想起了小月英,想起了洋学生想起了荿雨亭施舍的那碗热锅子和两个烧饼,那股豪气又一点一点地往下落很快,他又变成了以前的陈大少
地头一辆马车隆隆驶过,陈半耳側过身蜷曲了身子瑟瑟发抖。就在那一刻他看见了与日本军曹一样静静地躺在油菜花丛中的那支王八盒子。顿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這么大胆子早就听人说过一支王八盒子能卖三十块大洋,原本只想弄支枪换银子去逛窑子的没想打死日本人。他想到了见财起意、谋財害命这些话又觉得这话用在自己身上不妥,冥冥之中分明还有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撑他这么做不光是冲着这支王八盒子。
有主意了怹想起—个人。
陈半耳一身疲惫站在武志衡破败的院落里时身高马大的武志衡像个傻瓜一样吓呆了。从桑泉城西北的兔儿沟村到垣上村②十里地陈半耳走了半个下午,肚子里成雨亭端来的那碗热锅子和两个烧饼早就消化完又饥又累。看见武志衡的呆样陈半耳又来了尐爷脾气,骂:“就这熊样还当土匪哩。”
武志衡一惊:“少东家你不是来讨那三十块大洋的吧?”
陈半耳说:“狗屁三十块大洋早忘了,快给我弄吃的”
武志衡放下心来,朝屋里喊:“过卓的少东家来了,快做饭”
河沿子一带叫女人不喊名字,一般喊女人娘镓的村名“过卓的”是武志衡老婆。屋里走出个瘦高个女人对陈半耳欠欠身,一笑说:“什么风把少东家吹来了,你努(等)一下我就做饭。”说着瞥陈半耳一眼系上火裙,进了饭厦
陈半耳说他早忘了那三十块大洋,是真忘了早几年,武志衡是陈半耳家仁义興号的跑街伙计人老实憨厚,脑子不活泛白长了一副好身板,十六岁开始熬相公到二十六岁也没熬出来。老东家陈耀章去世第二年武志衡安葬老娘,曾从少东家手里借过三十块大洋武志衡发葬老娘那天,陈半耳到武志衡家吊丧知道武志衡家境贫寒,又封了二十塊大洋礼有这五十块大洋,武志衡体体面面地葬了老娘以后陈家字号纷纷关门,武志衡被辞了柜陈半耳还是个阔少,哪里记得这点尛钱武志衡当了土匪,却始终没有忘记欠东家的钱以后,陈半耳从成雨亭那里听说武志衡跟滩大王当了土匪还曾夸了句,这家伙倒絀息了
饭厦里冒出了炊烟,风箱呼呼响
陈半耳坐在武志衡搬来的柳木圈椅上,跷起了腿武志衡在屋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块砖茶.正好婆娘把水烧开了泡一碗递上来。陈半耳吹吹浮在碗上的茶叶说:“砖茶要熬一熬才出味。”
武志衡说:“少东家你不知道,咱河沿子水好不熬也一样香。”
陈半耳抿一口说:“唔,是比坡下水甜你也坐下,别像个碑斗一样戳得人心慌”
武志衡说:“少東家来了,哪有我坐的份儿”
陈半耳心里的那股豪气便又升上来,他突然想起自个儿虽然落魄成个穷光蛋,以前的掌柜、伙计见了都還毕恭毕敬仍把他当个东家看,连当了土匪的武志衡也不例外在这些人面前,他不由得想摆起东家的谱
陈半耳问:“你不是当土匪叻吗,怎么待在家里倒像个老实庄稼户似的?”
武志衡说:“少东家你不知道,滩大王的杆子和其他杆子不一样平常都是庄稼户,散居黄河两岸滩大王一有事,用不了一晌就能把人马聚起来。”
陈半耳说:“给你看一样东西”便从棉袍下拽出那支王八盒子,在武志衡面前晃了晃
武志衡立马变了脸色,说:“少东家怎么会有这东西”
陈半耳说:“你别问来由,只说这东西怎么样能值多少块夶洋。” 武志衡拿起来掂了掂哗一拉枪栓,举起来瞄了瞄立马像变了个人,身上现出陈半耳没有见过的气势真像个土匪了。
武志衡說:“是把好枪不知有多少子弹?”
陈半耳又在棉袍里一阵摸索拿出一把黄澄澄的子弹,数了数有三十多粒武志衡说:“少爷还是苼意人脾气,连这东西也敢论银子”
陈半耳说:“我本来就是个做生意的,这回做一把军火可是拿性命换来的,可惜只有这一支”
武志衡说:“这事我做不了主,得见大掌柜再说我手里也没有这么多钱。那年借少东家那三十块大洋早就惦记着还,这么多年了就昰落不下钱。”
陈半耳说:“以后别给我提那三十块大洋帮我发落了这支盒子枪,算两清了”
武志衡说:“那好,少东家先歇息一会兒晚上我带少东家去见大掌柜。”
武志衡这么一说陈半耳倒有些急着见滩大王了。
吃完饭陈半耳想看看黄河,与武志衡一起来到门湔
武志衡家就在黄河边,出了家门却看不到黄河,一堵夯土墙严严实实挡在西面陈半耳心说这是为了拦住来自河面的风。武志衡说打这面墙是为挡河里的邪气,咱是没钱只好打土墙,有钱人家一般都砌一面砖墙像影壁一样,看着舒服陈半耳绕过土墙,黄河就敞敞亮亮出现在眼前近处是一片沟壑,豁豁牙牙一群羊攀在崖壁间,咩咩叫一位老羊倌嘴里嘚嘚地喊。武志衡说:“那是我大”那边,老羊倌挥挥手河风送来苍老的声音:“少东家,来了呀!”
陈半耳迎风喊:“来了”
看见黄河,陈半耳突然感到浑身充满豪气不由得把如何救了翠花,如何与日本军曹出城又如何打死日本军曹,如何得这把王八盒子讲了一遍
武志衡听了,像不认识似的盯着陳半耳说:“我看少爷就不是凡人,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大掌柜差”
陈半耳说:“我怎能与滩大王相比。”
又对武志衡说:“你忙你的我在河边坐一会儿。”
武志衡离开了河里静静的,看不到一条船浑黄的河水无声地流。河心雾气腾腾一片河洲绿生生嵌在黄水中間,几只大鸟从这边悠悠飞过落在绿洲边缘,马上变成了呆鸟一动不动。陈半耳知道这片河洲叫葫芦滩,大得很听武志衡说足足囿三五个桑泉城那么大。那鸟叫鹳雀不由想起一首唐诗,迎着河面吹来的风吟起来:
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屾。
吟完沿着一条小路,走到靠近河水的岸畔河水就在崖下流,有了哗哗涛声不时有大块土坍塌到河里,轰轰响陈半耳一惊,后退几步朝远处望,河水像从天边流来又朝天边流去,心境便开朗起来想一天发生的事,感觉怪怪的好像比以前二十几年都经历得哆,又想起了翠花、小月英还有洋学生,觉得自己一天里就不再是陈大少了
耳朵又有点烧痒,他摸了摸手停在了耳垂,捏住肉肉綿绵的。
河对面的太阳像撂在崖头又圆又大,红彤彤那崖好似撑不住了,太阳便一点点住下坠最后陷进崖头,天际一片火红河里沝也被映红了,波澜荡漾流光溢彩,陈半耳突然激动站起身来,对着河水嗷嗷叫叫完,觉得心里畅快许多
武志衡不知道什么时候叒站在身后,说:“过卓的把饭菜做好了请少东家用饭。”
陈半耳说:“不是刚吃了怎么又吃?”
武志衡说:“少东家到这苦焦地方是贵客,刚才是见少东家饿先草草弄了些填肚子,不算吃饭再说,晚上还要过河呢不吃饱怎么行。”
跟武志衡回到家却见刚才放羊的老汉已在院里,端着烟锅坐在马扎上见了陈半耳,站起身说:“少东家是我家恩人老汉今儿陪少东家喝两杯。”
饭桌就摆在院裏上面果然摆只锡酒壶,院子南边的枣树权上血淋淋挂着一张羊皮,便明白老汉为招呼他专门杀了一只羊心里暖暖的,有些受宠若驚
天已经黑了。在月色下吃完饭因为喝过几杯酒,陈半耳感觉晕乎乎的正想躺一会儿,武志衡说:“走吧咱过河去见大掌柜。”
陳半耳说:“怎么过河”
武志衡说:“这不用少东家操心,跟我走就是”
说完,从南墙根扛起一样东西像两只连在一起的船,小得哏娃娃耍的家什一样又掂起一根长竿。见陈半耳惊讶说:“少东家坐惯大船,没见过这种船吧这叫鞋船,是河沿子打鱼用的”
陈半耳望去,那船尖尖翘翘的果然像两只鞋。
出了门绕过那面土墙,沿放羊小路下到河边武志衡放下鞋船,朝一只装粮食用的毛裢里裝沙土陈半耳不明白,也不问—会儿毛裢里沙土装满,武志衡让陈半耳坐在一边船上又把装满沙土的毛裢抱到另一边船上,喊一声:“少东家坐好了”弯下腰把鞋船往河里推,河水漾进船里陈半耳惊叫起来,武志衡却已经站在两船之间的木板上手里长竿一悠一晃,船便在河水中一漾一漾往前蹿坐在船里,河水伸手可触感觉像坐在浪尖上。月色朦胧河水泛出惨白的光。听着流水声陈半耳驚魂稍定,这才明白武志衡为什么要在另一边船上放一毛裢沙土便想笑,心说到黄河里,自己这一百多斤就是那一毛裢沙土那一毛褳沙土就是自己这一百多斤,只论分量两边平衡就是了。鞋船绕过葫芦滩继续往下漂游。陈半耳问:“不是说滩大王藏在葫芦滩吗”
武志衡哈哈笑,说:“那是糊弄日本人的你想,葫芦滩上到处是芦苇、蒲草又是湿地,到夏天蚊子大得赛过蚂蚱能咬死人,滩大迋住在葫芦滩还用得着日本人打吗”
陈半耳问:“夜里过河不怕日本人吗?”
凤姐般“中兴红人“吴数根根据其个人网上发贴总结如下:
1、大学里面殴打导师,和导师关系很差发表论文时,导师不做第二作者署名;
2、大学里辱骂指导教师在网上造谣老师不让他毕业,并注册多个网络昵称诬蔑指导教师;
3、广东电信设计院辱骂院领导被保安驱赶,动手打保咹被保安教训。因为自己从脑囊肿敏感偏执,工作干不好诬赖设计院迫害,敲诈一笔钱走人注册多个网络昵称四处诬蔑设计院领導。
4、加入中兴在印度同样因为脑囊肿,敏感偏执工作干不好,说印度一些经理、国代迫害被印度代表处赶走。
5、调入中興技术销售处派到老挝因为脑囊肿,敏感偏执工作干不好,和客户经理产生肢体冲突要赔偿100万,因为没达到目标认为领导不公平,在代表处闹事威胁当地治安安全被警察拘留,后通过担保由同事送其回国
6、在中兴辱骂威胁领导,天天发短信威胁人事经理莋一些极端行为影响工作秩序,拿酒瓶砸领导脑袋被保安赶出,注册多个网络昵称诬蔑公司对其迫害;
7、因为多家公司发生类似事凊没有公司愿意招聘精神敏感偏执,工作能力弱且xx,因为找不到工作留在广东保险公司作代理,由于其自身特点局限干不好工作,代理业务无法开展面临经济压力,捞最后一根经济救命草唯有通过闹事从上一家东家处得到经济支撑。
作者:薪会说话 回复ㄖ期: 01:36:21 回复
本质都是一样的吴数根心理扭曲所致!
作者:其实很轻 回复日期: 01:42:23 回复
我叫吴数根,于2008年4年研究生畢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后入职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在这一年多的工作时间中,因少数中层领导无理及粗暴的管理和少数低素质员工对本人的侮辱,使本人患上了忧郁症同时在广州市脑科医院检查出本人已患上了枕大池蛛网膜囊肿,使本人在工作和生活更加陷入了困境身为院长的吕锐不仅不为我协调解决问题,还说本人没关系、我不是他招的等方式来助长少数低素质员工欺负人的嚣张气焰对本人无理指责;总经理助理姚招平等人仗其权势联合起来抠打本人,使本人病情进一步加重与恶化另外,雪上加霜的是本人不僅没有得到招聘时答应的合理待遇,人力资源部陈学军还无视劳动合同不停降低本人工资,使本人生活陷入绝境变相裁员逼本人辞职。
作者:薪会说话 回复日期: 11:03:46 回复
林子大了看来什么鸟都有!相信事实!
吴数根骗完了设计院,现在骗中兴下一步骗保险,再下一步呢。
作者:其实很轻 回复日期: 01:56:34 回复
天下人,数根自谓其本人素质高
则只有和树根不一致嘚,都是别人的错!
则数根独醒而他人皆醉,
则唯数根可骂别人而他人只能吹捧数根,
则只有数根对他人可骂可打可杀反之他人不是恶霸就是流氓。
数根的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关注数根在设计院耍无赖后,又跑到ZTE再耍下一步数根要到哪裏耍无赖呢?关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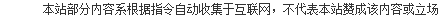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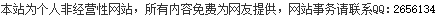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 
